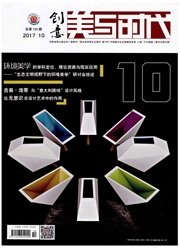欢迎您!东篱公司
退出

 中文摘要:
中文摘要:
从20世纪40年代尝试用新方法建立“新美学”的艰难“试验”到50年代“美学大讨论”中所遭遇的严峻“考验”,蔡仪总是陷入到历史的两难窘境中——不管是解放前作为理论“先知者”所面对的时代理论限制,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美学“孤寂者”所面对的美学围攻,蔡仪美学总是在屡遭非议与批判中处于一种“被边缘化”和“被改造”的角色状态中生存。这种历史的苦涩所带来的学理艰难其症结关键在于三方面:一是蔡仪所破坏的是长期主流的西方美学体系,而其美学建构中可资借鉴的唯物论美学话语资源却十分有限;二是在破坏“旧美学”的入手处,他以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”的唯物反映论的方法路径作为唯一“合法性”的美学原则;三是在美学的批判发展中,蔡仪总是处于学理的“捍卫”与“补救”上,而非方法论的彻底“反思”与“调整”,这种微观上的“自我补救”与理论完善注定只能是大发展中的小改动,于全盘无碍。
 同期刊论文项目
同期刊论文项目
 同项目期刊论文
同项目期刊论文
 期刊信息
期刊信息